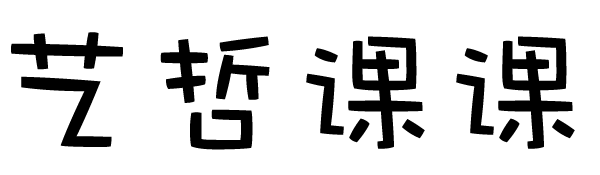教小学语文的博士校长是怎么读书的?

星教师︱徐俊(杭州市笕桥花园小学语文教师,副校长,教育哲学博士)
★★★
读书是一件超越功利的事儿。有时候,读书甚至可以和教学教育工作毫不相干,而是完全精神生命成长的需要。
我坚信,只有生命丰盈了,才能成为一个具有思考能力和决断能力的人,才能教好语文、做好校长。

儿时乱读书种下爱书的种子
我什么书都读。
小时候,躺在床底下的藤书簏旁边,读遍《隋唐演义》《三侠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,迷恋《老残游记》《三言二拍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,甚至沉醉在《再生缘》的越调、南吕、黄皮、慢板之中。
读这些书,比在榕树下听老人“说历史”有趣多了。“侠”之大者,“士”之清者,如同千年的古莲,埋在心底里。等青春沸腾的时候,这些种子便抑制不住地滋长,蔓延。
虽然读“侠士”书的种子当时并未发芽,却在我内心深处同时种下了一颗爱书的种子,而当我长大之后,那种“弹铗而歌”的冲动和“啸傲山林”的欲望,却也适时地发生了。
现在想来,儿时读书的力量,是强大的。
作为一个人,不管你是老师、校长还是学者,不管你是做教育的、科技的、医疗的,只要你不是绝世独立的,都需要这样的读书的种子,和从书中而来的人格力量的种子。
也因此,我又喜欢上了红楼、水浒、三国、西游,进而沉迷于半文半白的状态,喜欢上了《史记》《古文荟萃》和各种“观止”。这大抵是我还算勉强过得去的一点古文功底吧。
有人说,读书很费脑,很难静下心。其实,当你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,你会有一种“上瘾”的感觉,沉浸其中的幸福感,是“不可与他人语”的。或许也是因此,我在后来的语文教学、教育研究、文章著述中也总能很顺手地引经据典,这也算是读书的“副作用”吧。

△ 为了改写后给学生看,买了各个版本的《红楼梦》

读书也是“煮”书
读书也讲究火候,要文火慢炖,是急不来的。
偶尔,太阳温柔,风也清爽,天空也蓝得很,你可以擦干净地板,然后开一小瓶酒——红酒、白酒、啤酒、黄酒皆可,一小瓶就够了,在窗前的地板上,或躺着,或卧着,或坐着,就着酒,“煮”着书。
读书得用一个“煮”字。“煮”书就像煲汤,慢慢熬,不温不火,熬出味来。当“书香”四溢时,赶紧以墨水为调料,在书边上写下酸甜苦辣,这“煮书”的境界就出来了。
读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《艺境》,我就是在这种“煮”的状态下,让我在诗书画之间找到了共生点,在语文和艺术之间找到了平衡点,也让我在遇到崧舟先生时,能够轻易进入他那诗意语文的境界。
读这些书,真会让你有一种在语言和艺术的园地里漫步的感觉。
我的早晨通常是从中午开始的,然后在天色将晓时,枕着书昏昏睡去。
坐在被窝里“啃”朱光潜《全集》,啃《谈美书简》《悲剧心理学》《文艺心理学》《西方美学史》(朱光潜),“煮”李泽厚的《美学论集》《中国近代思想论》《美的历程》,顺带“翻炒”《傅雷家书》《艺术哲学》(傅雷译,丹纳名著)《孤独六讲》(蒋勋)《中国哲学简史》(冯友兰)《人的历史》《宗教的历史》《王国维文化学术随笔》《诗论》《诗品》《人间词话》《叙事学》《鲁讯论儿童文学》《张中行作品集》等。
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到现在,延伸到读各种教育教学专著。二十年前,还在读大学的时候,我硬是从每月百来块的伙食费里省下钱买了一套《名师教学思想录》。后来工作了,每年要花掉近五分之一的工资买著名教育教学专家的著作。
这些被我称之为“武功秘籍”的书,还包括戴汝潜教授主编的一套涵盖乐连珠“快速阅读”、张伟“球形阅读”等在内的教学理论书籍,贾志敏、于永正、支玉恒、靳家彦、张化万等先生的课堂教学实录,林崇德、皮连生等教授的教育心理学专著,以及“永远的经典”苏霍姆林、马卡连科、卢梭、佐藤学等的著作。
如果把文史哲类的书看作是“风味小吃”的话,教育教学专著则是“大菜硬菜”。正是因为杂食不挑,兼之文火慢炖,这些书的营养慢慢浸润着我的思考和实践,逐渐让我的思想丰满起来。
正因为有这样漫不经心的“煮”书的经历,才有了我几十堂“有据可查”的公开课,也逐渐形成了博观约取的个人教学风格;正因为有了驳杂的理论的碰撞和交融,才有了我上百篇“论有出处”的文章,有了《栖心斋·语文百日谈》《栖心斋·语文十年》等专著,也逐渐形成了基于哲学思辨的博士论文《生命与语文》,也才敢于以洋洋数十万字论述《语文教学的批判与重构》。

△ 徐俊老师的书房“栖心斋”,古色古香

从“一见钟情”到一读再读
人是有惰性和钝性的。读书也是如此。
如果把看电视纳入广义的阅读范畴的话,能看电视就不愿意读书,能读现代文就不读古文;形象有趣的愿意多品读、多玩味,艰涩难懂的读个大概就想跳过去。这是因为,生动有趣的内容,往往能让人一见钟情。
虽然时常为了“挑战自我”,也会专门啃些硬骨头,去琢磨些比较深奥的,或者说内涵比较深刻、意蕴比较丰富的文章,但更多的时候,我更喜欢那些读来让人不禁欣然或潸然的文章。很多猛一看书名,乍一翻前言,甫一读目录,就能让人“蠢蠢欲动”的书,都是我在文字里梦游的开始。
辛弃疾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就是让我“一见钟情”的,读到后来也是让我爱悠悠恨悠悠。
为了这首《清平乐》,我一读,再读,三读,四读,觉得不过瘾啊,又把《稼轩长短句》读了个遍,还翻阅了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,读了白寿彝《中国通史》与辛弃疾相关的章节,最后总算读懂了《清平乐·村居》,读出了一课《清平乐·村居》的教学设计。想想,越是懒人啊,越是愚人,到头来反倒因为偷懒贪趣而多费了工夫。但正是因为这种“一见钟情”的懒和笨,让我多读了书,让我身陷读书之福中而不能自拔。
比如读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始于大学时同学的推荐,也被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童话感动过,但当我因惦记着这个晓霞般美丽的故事而再读这本书时,却走进了孙少平的思考和精神追求。直到前不久再读这本书,我明白了孙少平“充满劳籍的同时也拥抱梦想”的诗意人生,也就更加满足于自己辛勤的劳作但精神非常光明的生活状态。
同样的,《穆斯林的葬礼》《最后一个匈奴》《巨流河》《南渡北归》《侧帽集》《饮水集》《红楼梦》,以及《繁星·春水》《飞鸟集》《新月集》《春花秋拾》《稻草人》等文学作品,还有《苏东坡传》《黄玉峰说李白》《黄玉峰说杜甫》《纳兰词传》《毛主席诗词鉴赏》等,都是我恋恋不舍,不知都了多少遍的书。因为“钟情”,很多书我买了各种版本,买了很多相关研究的书籍,一本一本翻阅,一次一次重温,也留下了不少痕迹。
比如读《美的历程》。
以前,纯粹是因为喜欢那种“徜徉在语言之途”的快意,可是,渐渐的,居然从美的起源读出了对语文的崇拜。我在自己的教育格言里写道:教育是门艺术,可这还不够。艺术来自何处?艺术来自图腾崇拜。如果每位教师都将教育艺术还原成一种生命的图腾,充满激情和敬仰地在教育的园地里安身立命时,那么教育便成功了。
这些心灵的启迪,都源自“一见钟情”贪懒愚笨的读书方法。实践证明,多读让人“一见钟情”的书,一读再读,书定不负你。

△ 为了带动学生写一手好字,拼命练书法

读书,谋求精神平等
谢冕说:我常想,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,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,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。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,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。
由此我又想,那些失去阅读机会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,他们的损失是不可补偿的。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,财富的不平等,权利的不平等,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。
对于这种精神的不平等,我想到了在崧舟先生身边时的一件趣事。
一日,学员们一起谈读书,聊语文,说艺术,兴致来了,先生挥毫泼墨,同门兄弟姐妹们约定,谁在先生落笔后最先猜出先生所写内容的出处,作品便归谁所有。一时间,诗情画意在工作室里流淌。我是那次游戏的大赢家。若非多读些书,岂非吃亏哉。
这是小事。最让我觉得开心得意的是聆听王先生讲座。常听有人说,好深奥,先生讲到的有些书和人听都没听过。而我则常常窃喜,因为我知道先生所言何义,所说何出。
就像张中行先生在《顺生论》里写的一样:这家底——是指谈文论理,钩玄提要的功底,大部分是由“读书”来的,小部分是由“思考”来的;思考的材料,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的,所以也无妨说,一切都是由读书来的。
张中行先生最有名的一部著作就是《顺生论》。这本书的精髓,也就是张中行先生的人生观,集中体现了张老先生作为“布衣学者”的精神境界。这句话来自《礼记·中庸》,一言以蔽之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”。率性是道,顺生自然同样是道,这道即通常所说的人生之道,用大白话说就是自己觉得怎样活才好。这位自周作人之后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,就是由读书而来的。《顺生论》以《我与读书》为代前言,写道“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,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那样的书”。
而我从书中获益最大的,除了有形的,如从冰心学会写诗,从辛弃疾、纳兰性德学会填词;更重要的是无形的,如从李白学会啸傲于钢筋水泥的丛林,从王国维学会明白了的人生的境界,从《美的历程》学会了生命的艺术的追求,从于永正学会了语文的严谨,从支玉恒学会了语文的大气,从靳家彦学会了语文的思辨,从王崧舟学会了语文的诗意,从贾志敏学会了语文的本真。

△ 给学生上课

读好书,成就理想人生
人间有太多不如意事。
能看得看清、看轻的,不外乎两种人:目不识丁的,或是读书读通透了的。前者如同六祖慧能,因为身无一物,目不识丁,便能吟出“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”;或如同苏轼的爷爷、苏洵的老爹,乡间老翁,也因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,方能在听闻儿孙一同高中时,依然淡然地在草垛底下啃牛肉,喝老酒。但这样的智者毕竟不多。很多人遇见点事儿,总能纠结郁闷,或是幸喜若狂,犹如“中邪”。如何“辟邪”?读好书可以。
傅雷夫妇给儿子傅聪夫妇的信(傅雷译丹纳名著《艺术哲学》的序)中得以论证。
傅雷夫妇在信中给儿媳弥拉推荐了莫罗阿的《恋爱与牺牲》《人生五大问题》,巴尔扎克的《两个新嫁娘的回忆》《奥诺利纳》——这本书通常和《夏倍上校》《禁治产》在一起编印。老两口除了通过推荐名著和儿辈谈人生,谈艺术,还谈自己对艺术人生的见解。
傅雷认为:自克里斯朵夫时代以来,西方艺术与知识界并无多大的改变——当然是在他那个年代来说的——诚实,勤奋,有创造力的年轻人,仍然得经历同样的磨难,就说我自己,也还没有渡完克里斯朵夫的最后阶段:身为一个激进的怀疑论者——年轻人通常都是这样的啊——年轻时习惯于跟所有形式的偶像对抗,又深受中国传统哲学道德的熏陶,我经历过无比的困难与无穷的痛苦,来适应这信仰的时代。”
这番话,这让我觉得,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,都是人生历练,都是幸福的。
正因为这样的书读多了,当我面对工作、生活中的起起伏伏,面对名誉、职位、个人利益的得得失失,才能免受其“邪”,保持心性的平和,正如傅雷得知傅聪的音乐会非常成功时说的,“知道聪能以坚强的意志,控制热情,收放自如,我非常高兴,这是我一向对他的期望”,我在书旁边写道:这不正是我所亟需的品质吗?
而信中所言“没有什么比以完美的形式表达出诗意的灵感与洋溢的热情更崇高了,为了聪的幸福,我不能不希望他迟早在人生艺术中也能像在音乐艺术中一样,达到和谐均衡的境地。”则成了我的理想——我的人生,我的语文生命,我的处世的诗一般的理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