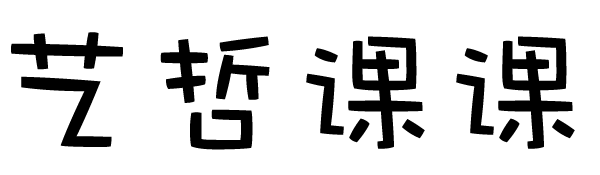我在女子监狱当管教:看起来越无辜的女性,可能越危险 | 女子杀人动机01

大家好,我是陈拙。
我最近认识了一个风趣的朋友。
她是一位叫秦三嬢的女狱警,90后,还是个女rapper,没事时爱好在监狱里写情歌,歌词大概都这种:
“hey bro ,虽然我现在身体被困住,但我的精力不会被束缚。”
半年前,她找到我,说想记实下女监中的故事。
那是一个特殊的犯人,此人是女监中最简单,且相对美丽的一个三十岁女人。
然后接触一段时间过后,秦三嬢烦闷得好久都没有再唱歌。
在女子监狱当管教八年了,我总是觉得,我不够了解这些日夜相处的女犯们。
范水仙终于还是被人打了。
听到这个消息,我还挺意料之中的。
她在监狱里人缘一直不怎么样,要说为什么,大概就因为她太卷。
一天到晚总是闷头干活,劳动产品好得能拉高车间消费标准,想躺平的犯人就看她不顺眼。
况且她还长得挺漂亮,三十多岁了,仍旧唇红齿白眉清目秀。
她也知道自己好看,还拿工分换雪花膏擦脸,拿着雪花膏的塑料盖子当镜子照来照去。
不喜欢她的女犯人们就会看热闹不嫌事地面说她,“妖得很”。
范水仙一般都不回嘴,就吃哑巴亏。结果越老实,越被排挤,这不,还是被打了。
我一边往车间跑一边想,真是人善被人欺,结果刚冲进车间,就听见一个女声在大喊:
“你们把她放开,我倒要看看她能有多厉害,老子人都杀过,还会怕个婆娘?”
声音的来源,竟然是范水仙。
我以为她正被另一个女人薅着头发,眼泪汪汪,结果是两三个女人拼命拉着她,生怕她上去把对方撕了。
范水仙竟然会骂人?——范水仙竟然是个杀人犯?
来不及多想,我赶紧把两人分开。
边上的女犯告诉我,两人是因为产品返工闹起来的。
她们流水线上有个刺头,总做不好东西,连累别人一起返工。
这回返工时,她一直在那叨叨说范水仙活儿做得不好,想甩锅给范水仙。
范水仙不理她,她觉得被忽视了,反过来骂范水仙“装清高”,“私底下还不知道是什么贱货呢!”
这句话好像戳到了范水仙的雷区,范水仙刷一下站起来骂对方,“早上吃的是屎吧?嘴巴那么臭”。
我们都没见过范水仙骂人,谁知道她一开口这么毒。
那刺头脸都红了,俩人就这样差点打起来。
我板着脸把范水仙拉进了谈话室。一进去,范水仙就卸了担子似的,神态轻松地说,警官你扣我的分吧,我都接受。
我盯着她,脑海里飞速运转应该怎么回答。
干狱警也有几年了,大部分情况下,我还是能认出谁是重刑犯的,她们一般分两种:
要么无法无天,来坐牢跟当皇帝一样;要么一脸的苦大仇深,话里话外有一种很沉的负罪感。
而范水仙,性格那么好,个人改造记录上还写,“我觉得我之所以坐牢,多少有点运气不好的成分在着”。
看起来就是个犯了小错的倒霉蛋。
所以我一直没有去查过她的案底,对她也没有什么戒心,突然知道她是个杀人犯,还有点紧张。
我故意反问她:“所以吵个架,心情很好?”
范水仙认真地回答我说,要扣分心情不好,“但是为自己发声的感觉太好了”。
她的脸有点红,像是刚才吵架激动的,但带着笑意,看起来眉飞色舞。
作为一个杀人犯,她觉得“为自己发声”就是骂另一个女人“吃屎”?
这也太奇怪了。大概安抚了一下范水仙的情绪后,我很快找时间去翻了她的档案。
档案写得很简单,大概就是说,她和另一个叫做“于小新”的人,由于感情纠纷,一起杀死了一个“宋某”。于小新是主犯,她是从犯。
惊悚的是,这是一起案中案。
警方调查发现,在本案的3年前,“于小新”还曾经杀过一个人。
也就是说,范水仙和一个杀人犯同床共枕了3年,最后又和他一块,杀死了另一个男人。
再下一次见到范水仙的时候,我就忍不住试探地说:“你这个案子有点神奇啊?”
范水仙有点不好意思地笑。
我问她到底怎么一回事,她轻叹一口气说,其实,怪就怪她之前不会像和刺头吵架时一样,对那个男人说一句“不”。
范水仙认识于小新的时候,还不到18岁,而于小新曾经是一间修鞋铺的老板。
但当时最吸引范水仙的,不是他的年少有为,而是他的孤傲。
于小新跟她说,他是浙江人,家里有三姐弟,母亲嫌弃父亲穷,在三姐弟年事还小的时候,跟着同村的一个男的跑了。
三姐弟从小没有母亲关爱,都是早早停学,各奔东西。
于小新初出社会的时候只有十三岁,很多地方都不敢招童工,他就只可去打黑工,饥一顿饱一顿的,从浙江漂泊到了南方。
等他攒下钱,自己开了一家修鞋铺,想要把家人接过来过好日子,才得悉父亲已经去世,姐姐弟弟也不愿意过来。
因此他在这儿举目无亲,只有一个人。
范水仙从小家庭和睦,于小新表现出的成熟和孤独,深深地吸引了她。她决心要由自己来给这个男人一个家。
开始范水仙的父母并不同意,觉得于小新是外地人,亲戚朋友一个都没见过,不能知根知底,怕水仙吃亏。
但范水仙第一次忤逆了父母。
她拿爸爸从小说的“助人为乐”当借口,反过来劝父母说,那我们不是应该把这种家庭的幸福带给于小新吗?
父母大概也被范水仙的倔强打了个措手不及,最后还是同意了。
她在不到20岁的年纪,就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。
这可是我长久以来的理想之一,我很想为范水仙激动一下,可是她对此只有后悔。
她露出很惆怅的表情,问我,是不是她就不该自己做选择?
结婚几年,水仙觉得于小新哪里都好,但身边的其他姐妹都觉得于小新大男子主义有些严重。
有的时候,于小新会板着脸跟她说,不许做对不起他的事,否则后果就会很严重。
但范水仙也说,每次凶完,他又会恢复温和的神情,安抚范水仙说,只要听他的,他就会对她好一辈子。
她觉得,有点大男子主义是男子气概的表现,毕竟这个男人是自己选的,只要自己顺着他点,俩人就会过得很好。
但宋明浩出现了。
他是范水仙公司的空降兵,刚来公司,就有很多同事传说,这人背景大得很,是被家里人送来找点事做的,和范水仙他们这样的普通员工不是一类人。
也许就因为这样,单位上很多同事,尤其是年轻未婚的女同事,都喜欢扎堆围在宋明浩身边,叽叽喳喳的。
范水仙当时已经结婚,也不喜欢宋明浩这种花孔雀的性格。
尤其有一回她听见宋明浩开黄腔之后,更是对他敬而远之。
没想到宋明浩不知怎么就看上她了。
他上班时总是故意打趣范水仙,一次两次没有回应,接着又送点小东西。
同事们传绯闻,他也不反驳,甚至下班后也故意“偶遇”她,约她出去吃饭。
范水仙说自己从来没搭理过,可是一年多的时间里,范水仙怀了个孕,生了个孩子了,宋明浩还没放弃,甚至愈演愈烈。
直到有天,范水仙下班回家,看见丈夫于小新脸色阴沉地坐在沙发上,盯着她问:
你和宋明浩到底是什么关系?
范水仙说,其实丈夫知道宋明浩,她没少跟他抱怨这个富二代死缠烂打,也是丈夫跟她说“惹不起躲得起”的。
但当时她觉得,于小新身上莫名有一种恐怖的感觉。
他掐着一根烟,烟灰堆了老长,他手动都不动。
她才知道,就在那天下午,宋明浩竟然跑到她家跟她丈夫“宣战”了。
他跟于小新说,他俩早就在一起了,甚至说于小新是绿头乌龟,替他养孩子。
当时她有种错觉,要是今天自己没法说服丈夫,他能把她生吞了。
那几分钟无比漫长,范水仙拼命地发誓、辩解,把所有跟宋明浩的交集都一五一十说了又说。
于小新的目光在她身上转来转去,好半天,突然一松。
他温言细语地跟范水仙道歉,说自己不是不信任她,就是自尊心作祟,情绪失控了。
范水仙说她可以辞职,于小新摇头,说这不是长久之计。
“他都敢闹上门了,以后街坊邻里怎么看待我们,怎么看待你,怎么看待我们的孩子?你总不想咱们的孩子在闲言碎语里长大吧?”
这好像真的很严重,范水仙问他那该怎么办?
于小新紧紧抱住她,反问:“敢不敢整死他?”
范水仙没有拒绝。
她跟我解释说,她是怕于小新生气。
这个丈夫是她自己选的,她必须得“出嫁从夫”。
从小爸妈就教她,“一定要会看人脸色,凡事要考量自己占不占理,占理了要看自己得不得罪得起……”
丈夫、父母,都是得罪不起、不能拒绝的。
初中毕业,父母说她“没有读书的命”,让她休学,她就休了;宋明浩追了她几年,她不答应也不敢说什么;到最后丈夫说要杀人,她也只敢应和。
我想起我大学毕业那年,我妈硬逼着我回老家考公务员,还非要考监狱岗的时候。
说实话,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妈为什么就觉得监狱岗“稳定”,可我也不敢拒绝我妈。
小时候,我被她在街上掀翻了暴打,长大后也像戴着锁链的大象一样。
我根本不敢想象要对他们说“不”,就从这点来说,我好像没比范水仙强到哪儿去。
不同的是,范水仙得到的要求,是去杀人。
于小新给了她一个傻瓜式的杀人教程,第一步就是让她去约宋明浩,周末一起爬情人山。
那座山有两个传说,一是如果相爱的情侣一起爬,就能相守到老;二是正相反,如果两人当中有人有异心,就会不得善终。
不过三个人大概都没有在乎这个诅咒,宋明浩如他们所料,喜出望外地答应了邀约。
出发前的晚上,于小新带回家一瓶药片,用水溶解,然后又拿注射器打进了纸袋装的牛奶里。
范水仙说,他告诉自己这只是安眠药艾司唑仑。
“你只要负责让宋明浩喝下它,剩下的交给我,你们女人干不了”。
第二天早上,范水仙跟着他提早到了山脚的小卖部,买了爬山的零食,把加了料的牛奶混在里面。
于小新拿着两盒牛奶跟她比划,要给宋明浩喝的这瓶牛奶的盒子,右下侧用刀割开了一个小豁口,千万不能拿错。
范水仙只知道点头。
于小新接着又叮嘱,一定要确认宋明浩把牛奶喝完,一旦他有了“反应”,就及时联系自己,如果药效不够也没关系,想办法通知自己就好。
范水仙还是点头。
其实她当时已经紧张坏了,话都说不出来。
于小新看着她突然笑了,跟她说别紧张,说就算这次不成,下次也可以再想其他办法,总之有他在一天,这个事儿就一定会料理好。
一看他笑,范水仙又觉得没事了,只要她听他的,俩人还会过上好日子的。
她提着塑料袋,跟宋明浩一块走上了情人山。
宋明浩看起来比以往都要高兴,一路都没察觉什么异样。
到了半山腰,范水仙喊累,在亭子里休息,一边就找出牛奶递给了宋明浩。
宋明浩接过牛奶,喝了一半,忽然砸吧着嘴说,这牛奶有点苦。
范水仙心脏狂跳,但她的行动却出奇的冷静。
她笑着从包里翻出了整瓶的安眠药,反问宋明浩是不是感冒了嘴巴苦?要不要吃点感冒药?
宋明浩满眼感动地摇头,喝完了整瓶牛奶,继续和她聊天。说着说着,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,接着就靠在范水仙肩上睡着了。
范水仙试着喊他、推他,人都没醒。
她愣了半天,才给丈夫发送了那条短信:
“你可以来干活了。”
于小新很快出现在山路尽头,她这才知道,丈夫其实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后面,怕出什么差错。
她觉得很安心,甚至有点感动。于小新让她提前离开,说她见不得这些,她就下山了。
但下山路走到一半,范水仙突然想起来,丈夫叮嘱过自己,牛奶盒一定要记得收走,省得留下什么痕迹惹麻烦。
宋明浩喝完牛奶就把盒子扔进了亭子边上的垃圾桶,于小新清理现场大概率看不着。
她越想越心虚,决定折回去提醒丈夫一下。
她回身往山上爬,渐渐靠近观景亭,隐约听见“砰、砰”的声音。
范水仙不知怎么的心里有点发毛,快步绕过树丛,终于弄明白了这个声音的来源——
她的丈夫、她的枕边人于小新,正在用一把砍刀,一下一下地剁着另一个人的头。
范水仙说,于小新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己的选择,但没想到,就选错了。
事后想想,于小新其实早就有疑点。
结婚后没多久,两人有了儿子,范水仙要给孩子落户口,得跟于小新扯证。可就在这个问题上,两人吵得天翻地覆。
于小新拿不出户口本。
最开始他说,户口本丢了,因为前些年到处打工,不知道放哪了。
范水仙催他补办,他又说店里太忙,等得空再去。
再到后来,他直接不耐烦地告诉水仙,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户口本。
最开始范水仙怀疑于小新就是不想跟她领证,甚至外面有人。
但再追问的时候,于小新越来越不耐烦,甚至阴沉沉地冒出一句:“你确定你敢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户口本?”
范水仙说,当时她完全被吓住了,一句也不敢追问。
直到杀死宋明浩的那天,范水仙才彻底明白了。
她看见她的丈夫骑在宋明浩的身上,背对着她,高高举起砍刀,重重落下,砰的一声,好像从她脑子里传来的一样,非常沉闷。
整个亭子里都是血腥味,两个人身上都是鲜红的。
似乎是骨头终于被砍断了,丈夫伸手拨弄了一下,挑了一个角度,又是几刀下去,一整颗头颅忽然就滚了下来。
那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做的,那甚至不像一个人。
范水仙直接扑通跪坐在地上了。
于小新猛地回过头来,看到是范水仙,他似乎松了一口气。
他还像没事人一样,单手把地上的东西抓起来,问范水仙要袋子。
范水仙讷讷地从兜里掏出塑料袋递给他。
于小新自顾自把东西装好,打了个死结,又递回给范水仙。
范水仙不敢接,于小新没好气地说,我还有事要忙!
他指的是还要收拾剩下的“东西”。
范水仙只能自己去抛尸。
那袋东西具体多重,什么感觉,她拎着它走了多远,扔在哪里,范水仙一点都不记得了。
回过神来,她已经和丈夫回到家里开的擦鞋铺。
于小新跟她说,一切放心,尸体处理得很干净,就算有事,“我拿命保护你”。
但是这一次,丈夫的安抚不像之前那样有效,范水仙不但怕被抓,甚至还有点怕他。
她心里已经隐隐猜到,这可能不是丈夫第一次杀人。问题是,这一次她成了他的帮凶。
范水仙越看于小新越害怕,晚上丈夫想亲近她,都被她以各种理由拒绝。
她又一次把走神烧糊了的菜端上桌时,于小新没动筷子,盯着她不说话了。
“你实话说,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?”
他把她的紧张和拒绝当成了心虚,反而对范水仙生了疑心。
范水仙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:他会把我的脑袋也砍下来的。
她慌忙摇头,绞尽脑汁发最毒的誓证明自己。
看于小新还将信将疑的,她着急了,跑出去拿了把剪刀,抓着儿子就给他剪头发。
孩子哇哇大哭着反抗,她只剪下来一小撮,攥在手里递给丈夫,说你拿去做亲子鉴定,一定是你亲生的,不是你把我杀了。
于小新又看了她一会,像在打量她,又像在欣赏她的难堪。
最后,他终于点了点头,安抚她说你放心,只要孩子是我的,咱俩不管出什么事,我一个人扛。
范水仙心里的压力一泻千里,眼泪哗哗流出来。
她后悔了。她真的后悔了,她就应该听爸妈的话,不要嫁给这个男人的。
我来监狱的时候,范水仙已经坐了十多年的牢,可是“选错了丈夫”这件事的阴影,似乎仍然停留在她身上。
十几年了,她永远低着头,不和其他女犯聊天,不东张西望,就是静静地做着自己手里的活儿。
每次我按例找她谈话的时候,她都以为自己是做错事了,话没说三句就开始道歉,搞得我也怪尴尬的。
因为她被排挤、帮人返工的事情,之前我还找她组长谈过话。
结果范水仙知道后又屁颠颠地跑来跟我说,千万不要误会组长,她通过这段时间帮别人返工,学到了很多工艺技巧,“为之后的改造奠定了基础”。
这心态,我好像能看见她在山上,被递了一个血淋淋的塑料袋,还只敢跟着走的样子。
后来我和范水仙聊她的案子的时候,每一次她叹气说都是她的错,都是她选错了丈夫,我都有些犹豫。
在我看来,想要勇敢追爱不是什么问题,真正的问题出在于小新身上。
在他们被捕后,于小新的真面目终于水落石出。
最后一次审讯的时候,办案民警曾问过范水仙一些奇怪的问题:
“你认识李继伟吗?”
“你了解你的丈夫于小新吗?”
“于小新有没有和你说过任何关于李继伟的事情?”
范水仙当时很懵,再下一次听到“李继伟”这个名字,就是在法院庭审的现场了。
法官在庭上宣读:“被告李继伟,化名于小新……”
范水仙只觉得脑子懵了一下,才反应过来,这意思是说她的丈夫就是李继伟。
于小新和范水仙所讲的童年经历和打拼经历都不假,但他却自始至终没有向范水仙坦白过,他还有“李继伟”这个名字。
而李继伟,是一个在逃杀人犯。
在范水仙认识“于小新”的几个月前,李继伟正在四处打工。
那时候的工人们常常坐在迪厅门口打牌,跟小姐过过嘴瘾。
李继伟嫌他们“脏”,但还是时不时要去那里找工友搭伙儿,并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一次,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
卷宗上没有写明那是什么对话,也可能李继伟也不记得了,只说是“污言秽语”。
李继伟莫名被那些话激怒了,他说,他觉得自己要“为民除害”,杀死这个小姐。
这种对“荡妇”的仇恨,可能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悲惨经历都归咎于年幼时母亲的出走,可能是因为别的,我不得而知了。
我只知道,李继伟供述,他带着刀埋伏了那个女人好几天,但就是不巧没有遇上那个女人落单。
但就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,正好遇到了另一个走夜路的女孩。
李继伟觉得,这么晚出门的,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于是他把她用刀劫持到路边树林中,实施了奸杀。
当天晚上,他就离开了这个打工的地方,换了一个名字。
检察官在法庭上难掩愤怒地说,其实,那个受害女孩只是一名普通高中生。
她走夜路,仅仅是因为家里人不让她夜不归宿,她赶着从同学家回去。
被害那年,她只有18岁,她和范水仙,几乎一样大。
不到18岁就嫁给了这样一个男人,被怎样PUA都不奇怪。
在我跟范水仙聊她的案子时,范水仙经常唉声叹气地说,她觉得她的问题是不该不听爸妈的,嫁给于小新。
可是我觉得,她最大的问题明明是不该没有主见,不会拒绝宋明浩,又不会拒绝丈夫要求她一块杀人。
我是有一点私心,我觉得她太像我,乖了一辈子。
范水仙好像真听进去了,她说是的,经过今天这一架,她发现勇敢说“不”或许会更好。
打那以后,范水仙就成了我们这儿有名的刺头,给她饭少了,给她活多了,她一点就炸。
渐渐的,监狱里真的没什么人敢欺负她了。
我对此挺欣慰的,又一次闲聊的时候,我跟范水仙说,感觉你现在状态挺好的,如果你私底下发现什么情况不好和其他人说,你就跟我说吧。
我是暗示她,可以做我的眼线。范水仙乖乖地答应了。
没几天,她就来跟我举报,有两个人洗澡的时候过于亲密——
“太不要脸了,两个婆娘洗个澡粘在一起扭来扭去的,从上摸到下,那么多人看着,太恶心了,我都不好意思说”。
我听她的去查了那两个人,确实发现她们有些特殊的接触,于是安排把她们分开,并表扬了范水仙。
范水仙给我的举报越来越多,比如某某某偷偷传纸条,某某某藏吃的。
她的口头禅也变成了:“你们最了解我这个人了,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不会乱说的。”
她好像一点也不怕得罪别人了。
但没多久,我开始收到关于范水仙的举报。有人说她收别人送的东西。
我再一查,发现给范水仙送东西的女犯人,之前和那个传出澡堂八卦的女犯人,也有些不清不楚的关系。
原来这是一桩三角恋,被甩的女人鼓动范水仙来打小报告,实际是为了报复前任。
而范水仙也不像她表现的那么大义凛然,是为了别人送她的好处。
我心情有些复杂,觉得事情好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。
我同情她的经历,希望她不那么乖,可是她却反过来利用我的纵容牟利。
我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好,在跟别的犯人谈话时,忍不住又说起了范水仙。
我说觉得范水仙也是犯了错,对方连连点头,说,我觉得她还是可怜的,换做是我,如果有人要伤害我的家人,我也会走到那一步。
我心里一紧,伤害家人?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件事?
那个女犯人困惑地看着我,说,范水仙跟所有人都说,她杀人是因为那个姓宋的一直死缠着她,还说如果她不答应,就把她儿子杀了,毁了她家。
范水仙杀人不是因为于小新的教唆,而是因为宋明浩的威胁吗?
这性质一下就不一样了,对于一名狱警而言,报复心强的犯人,和由于盲从犯案的犯人,处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我被范水仙骗了?
找她对质的机会很快来了。
在一次亲情电话后,范水仙自己找上门来了。
她问我知不知道外面在流行什么游戏?为什么她儿子这么沉迷,还总是喊着“杀杀杀”的。
我猜想她是想到了已经被枪毙的于小新,担心有什么“犯罪基因”,于是一通劝她,相信教育,相信大人对孩子引导的力量,之类的。
紧接着,我把话题转向了她自己,我问,那你觉得自己作为妈妈,是一个诚实的人吗?
范水仙突然沉默了,低头良久,最后突然说:“其实我和他睡过。”
我没反应过来,问:“谁?”
她说,“宋明浩,我跟他睡过。”
在和丈夫因为户口问题争执不断的那段时间里,有一回,范水仙在争吵后气得夺门而出,正好在门外撞见了宋明浩。
宋明浩可能是听了会墙角,知道发生了什么,上来就跟她说,既然心情不好,不如跟他喝酒去。
范水仙真就跟着他去了,酒过三巡,两人半推半就地发生了关系。
范水仙说,醒来的那一刻,她真的非常害怕。
她跟我讲了一个小时候的故事,说那时候村里有一个外村嫁过来的长得很漂亮的孃孃。
因为她说话温柔,又经常给小孩子糖吃,他们小娃都爱去那个孃孃家门口晃悠。
但后来有段时间,这个孃孃就不见了,听大人们说,是和她男人出去打工了。
再见到那个孃孃的时候,她被她男人用皮裤带把手往后绑着,往屋里拖拽,男人一边骂骂咧咧,一边往那孃孃身上吐着唾沫。
村里的小孩再去要糖吃,回家都会挨爸妈的揍。
边揍边说,“不准再去那个烂货家门口晃”之类的话。
从那天起,母亲就会经常教育水仙,小姑娘家要自爱,以后嫁人了就要听丈夫的话,不能和别人乱搞,要不像那个谁一样被人拖着回来打成这种逼样,老祖宗的脸都要丢完掉的。
她记得母亲的话,记得丈夫的那些异常。在她眼里,这不是一次“出轨”,而是致命的。
范水仙说她劝过宋明浩当什么都没发生过,但宋明浩一幅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,反过来要她离婚跟自己过。
范水仙说自己还有孩子,宋明浩开玩笑似的说,那要是你孩子没了,我们就可以了?
从他的话里,范水仙嗅出来一丝危险的预兆。
没几天,她就从丈夫口中得知,宋明浩上门来了。
幸好这次他没有说出什么,幸好这次丈夫还相信了她,但下一次呢?
对不贞的恐惧、保护孩子的决心,和丈夫的怀疑,是这三个因素,一块让她问出了那个问题。
“那你拿个主意吧。”
在丈夫愤怒的时候,她垂下眼睛,凑到他跟前,哀求地、软弱地问那个她明知可能杀过人的丈夫,那你拿个主意吧。
她把一切都交给了丈夫,就像她让我来决定找她做眼线,让狱友决定同情她。
在被捕后,范水仙面对警察,一句话都没说,还反过来请求警察给于小新和儿子做亲子鉴定。
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因为于小新承诺过,只要孩子是他的,他就会“一个人扛”。范水仙想让他兑现诺言。
她大概觉得,决定杀人的是他,最后偿命的也应该是他。
但结果不是这样的,范水仙还是出现在了这里。
无期徒刑。她已经三十多岁了,仍然在向别人一次次地,颠来倒去地,讲述她二十几岁时那个故事。
她逃避了选择,可是终究没能逃避后果。
范水仙又来找我打小报告了,巡视车间的时候,她一直偷偷摸摸地看我。
我一跟她对视,她就示意我过去,然后轻声说,得空找她一下。
我把她叫到角落里,她又不说正题,一直抱怨着家里的事。
我不接话,她绕了半天,大概也觉得无趣,终于开始说到某某某,分配工作后不积极,“使都使不动”,“她呀,在你们面前是一套,在我们面前又是一套。”
我还是不接话,反问她:“你来举报别人,自己屁股擦干净了吗?”
范水仙一愣,笑了,直勾勾地看着我,撒娇似的说:
“没有啊,我能有什么事,秦警官,你是知道我的,我这个人,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。”
这是秦三嬢记录的第一个故事。
除此之外,她还给我讲了几个更离奇的——
有个女人决定杀死自己的丈夫,她花5万块雇凶杀人,这笔钱被倒了三手,最终五个杀手一起来到女人面前,把她和丈夫一起打晕带走了……
有个四合院里被埋满了现金,这是一个女人杀死情夫潜逃十年后,靠卖煎饼果子赚的钱。
女狱警秦三嬢记录的故事大多细思极恐。
女犯人们跟狱友们有一种说法,卷宗上记录着另一种说法,而等她们来到秦三嬢面前,又会告诉她完全不同的第三种说法。
秦三嬢记录下她在女子监狱中听到的所有故事,只为回答一个问题:
这些看起来柔弱又单纯的女人们,在来到这里之前,为何会选择举起屠刀?
本文链接: https://www.yizhekk.com/0248335968.html